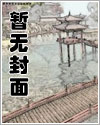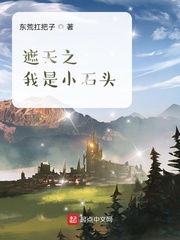在氮厂大门外,杨明辉与郭亮坐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,内心有几分激动。在新千年的吴县,农用三轮车仍是连接农村与县城的主要交通工具。即便这样的交通工具也只通达中心村镇,像柳河港那样偏僻的村庄,还有5公里的徒步距离。因为是放长假,大家都急切着回家,很快三轮上就站了足有十五六人,像筷篓里竖着的筷子,个个前胸贴着后背,一只手扳着自认为牢靠的地方。车上有人催促着驾驶员,那人便搪塞着再拉两个就走,随后便是长长的吆喊声。车厢里根本就再插不进一条腿了,等了几分钟,驾驶员见没了希望,车子终于开动了。
随着车子的行进,车箱里就像占卦的签盒,惯性所然,人们左摇右摆。杨明辉和郭亮像对抗着湍急的浪头,紧绷着身体,以保持身体平衡。车箱里一位五十多少的大妈哭丧声音,“我的老妈吆,这是遭的哪门子罪,早知不回了。”顿时,喊叫声、谩骂声、哭丧声混成一片,被迎面吹来的疾风拉的很长很远。
一个小时后,三轮到达目的地,人们纷纷跳车而下,付了车钱,就四散离去。杨明辉和郭亮归心似箭,背着干瘪的背包,疾步如飞,5公里的路半个小时就拿下,忘记了赶路的疲劳与饥饿。
国庆长假之于农民来说,忙碌、疲惫与喜悦并存。在这收获的季节,满眼是沉甸甸、红艳艳的景象。院子里堆如小山的是谷穗、高粱、糜子,摊开晾晒的是红枣、花生,还有不知名的绿豆、黄豆等豆类点缀其间。杨明辉站在脑畔上,看着冷冰冰的烟囱和妈妈董桂芳像蚂蚁一样匆忙的身影,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喊着,妈我回来了,而是默默地走回院子。
董桂芳被突然出现的的明辉吓了一跳,“臭小子,回来了也不吱一声。”立马放下家什,解下头巾,弹着身上的尘土,啪啪作响,“你看妈都忙糊了,忘了你们今天要回来,饿了吧,妈这就做饭。”
没等董桂芳说完,明辉就转身来到炭窑抱了一堆柴禾。回到窑里,董桂芳正麻利地清理着灶堂,鼻梁处不知什么时候擦上一秃锅灰,滑稽又好笑。明辉拿了毛巾,指着黑点,“妈,你准备唱戏呀?”
董桂芳不好意思地笑着:“想吃什么?妈给你做。”
“我不饿,我爸呢?”都说饿了想到妈,饱了记得爸。杨明辉刚压住了饥饿的叫唤,才想起好像未见爸爸的身影。
“你爸在对面的山坳里捡枣呢。”董桂芳拉着风箱,有股浓烟从灶口冒出来,拿着竹编使劲扇着。
此时,天色已暗下来,火红的光线穿过灶头映到董桂芳的身上,随着拉杆的伸缩,在墙上投下一个忽大忽小的黑影。
明辉起身来到后窑掌,提过一筐土豆,拿起擦子,给土豆削皮。这时,院里外面传来妈的叫声。只见弟弟杨明伟和妹妹杨明艳刚一进门就直叫唤着:“饭熟了没?快饿死了。”
见明辉在后面蹲着,道:“哥也回来了?”
“我也刚回来。”杨明辉应着声。
“我们吃什么?”杨明艳端了盆清水,洗着明辉削完的土豆。
“洋芋擦擦。”董桂芳把锅里的开水一瓢一瓢地灌进暖瓶,由于窝着气,壶塞处发着“扑哧扑哧”的声响。
“有肉吗?”杨明伟显然多日不知肉味了。
“有,在大立柜里,我前天小炒的。”董桂芳知道孩子们一定想肉了,特意在前天的集市上割了一块。
明伟欢舞着双手端出一碗小炒肉,拿筷子往另一个碗里分了一些,把剩下的放回大立柜,倚身望着热情腾腾的大锅,嘴里嚼得津津有味。
“二鬼,猴急甚了,小心肚子疼。”董桂芳心疼道。
杨明伟冲董桂芳使着鬼脸。
“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呢?”明辉看到饭快熟了,天色已黑,担心起了爸爸。
正欲出门,听见院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扁担咿呀的叫唤声。
“爸,怎么才回来?天都黑了。”明辉闻声而出,打亮手电筒,急切地询问道。
“就剩这一回了,再去一次划不来,所以熬到现在。”明辉父亲杨世尧放下扁担,用毛巾揩完汗水,取下腰里别着的烟袋。
“那也不急这一时?有我们三个呢。”杨明辉心疼道。
“明天还有其他安排,赶着秋雨前把红枣抢回来。”杨世尧划亮一根火柴,放在烟锅上,猛吸两口,顿时口鼻喷烟,嘴里嘶嘶作响,托烟杆的指头轻按着烟锅里的烟草,很舒展惬意的样子。
“爸,你少抽两口,那样对身体不好。”明辉看见爸爸杨世尧由于用力抽烟深凹下去的面颊,更加消瘦如柴,劝道。
“死不了,庄稼人,没那么娇贵。”杨世尧由于话说的急,一口气没换过来,一阵咳嗽。
“掌柜的,吃饭了。”屋里传来董桂芳的呼喊声。
杨世尧猛吸了几口,确认烟草已烧完,烟锅在鞋底磕得崩崩响,而后细致地清理着烟具,一丝不苟。
屋里,一盏白炽灯昏黄。大口锅里热气腾腾的洋芋擦擦在肉香的萦绕下,更增添了几分食欲,锅底是甜蜜的南瓜汤。一时间,屋里发出一阵急促的筷子碰击碗边的清脆声,而后是咕噜噜的饱嗝。
饭后一口烟,胜过活神仙,是杨世尧的人生箴言,此刻,正坐在门坎上吞云吐雾。杨明艳正帮着妈妈董桂芳收拾着碗筷。杨明辉和弟弟杨明伟躺炕上,轻拂着肚皮,助力肠胃消化的功能。
“明到大后天,争取把红枣打完,红薯和高粱一天,扳玉米棒子得一天,再安顿上一天,娃们就收假了。”杨世尧边吐着烟圈边自顾安排着国庆长假的农活。
在杨父眼里,学习固然重要,但那是在学校的事情。回了家,干活儿是第一位的。尤其在秋收的季节,遇上秋雨多发的时候,白天和晚上连轴转是常有的事。用杨父的话说,一年都熬下来了,总不能在关键时刻出岔子?十几年过去了,杨世尧的身躯日渐佝偻,但对土地、粮食的敬畏之心未有丝毫亵渎。
红枣是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,抓住重点保收入是杨世尧笃信不变的圭臬。这几年红枣在市场上走俏,价格也水涨船高,1斤1-2元,上门收购,是农民增收稳收的不二法宝。为此,杨世尧春修剪、施肥、灭虫,夏浇水、打芽、锄草,对枣树呵护有加,而且大力培植早苗,扩大规模,增加产量。几年下来,一年红枣收入达四千元。按一个小工一天15元的收入来算,四千元可是一年都难以实现的目标。照理说,杨家一年纯收入五六千元应该是不错的了,问题就在庞大的教育支出,让一家生活过的紧巴艰难。
杨明辉弟妹三人一周按45元算,一年40周就是1800元,加上报名费1200元,课本费600元,学杂费500元,只教育支出一项一年就得4100元,占据总收入的68%,而且不赊不欠。这是装在杨世尧心里的一本烂账,也是杨家三兄妹头上的紧箍咒。
吴县历来秋雨颇丰,抢收红枣的事情不敢有半点马虎,秋雨连绵是脆生生的红枣的克星。枣一烂,就发霉,就像得了灰指甲,一个传染两,狗屎一堆,没人过问。
杨世尧没有别的能耐,供子女读书成为跳出农门的唯一希望。再苦再难也要坚持,就像负重爬坡过坎的老黄牛,哪怕累死,也不退步。杨明辉三人学习如何,杨世尧并不太在意。老话说的,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的娃娃会打洞。他杨世尧大字不识,能有龙凤种乎?但有一点,读书肯定比不读书要强。
正是这样的认识和行为方式,使得杨家三子女比同龄的孩子早熟一些。做家务、下地干活样样在行,对父母含辛茹苦的理解也更深刻,减轻家庭负担成为他们赎罪的共识。
父亲杨世尧的安排无可厚非。一家人难得的团圆让杨明辉暖意融融。话题自然由收成到农活,再到村里大小新闻,最后到各自学习生活、校园趣闻,老师同学,兴之所至,开怀大笑,其乐融融。
杨世尧看着一贯冷清的家里,又有了往日的热闹,拉了一会儿话就在院子里忙活开了。董桂芳打扫着屋里,时而插上一句话,望着日渐长大的孩子们,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。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,她一手拉扯大三个孩子,是多么的不易啊。老大杨明辉沉稳懂事,老二杨明伟调皮好动,女儿杨明艳贴心勤快。作为母亲,董桂芳不奢望他们大富大贵,只愿子女个个健康成长,平平安安。
农忙时节,董桂芳起早贪黑,虽然累得腰酸背痛,但有盼头,干劲足。她相信通过双手辛勤劳动,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。忙里偷闲了一阵,董桂芳还是来到硷畔上,开始摘着花生,这样才觉得安心踏实。
农历九月初的秋夜,单衣薄裤,坐在面风的硷畔上,一阵微风吹过,冷颤直抖。杨明辉借着昏暗的灯光,辨出了董桂芳的轮廓,也搬了节木桩过来,坐下摘着花生。
“明辉,夜凉,回去早点儿睡,明天要早起。妈一人摘就行了。”董桂芳打劝着。
“妈,地里还有花生没?”明辉没有接着妈妈的话头,而是想起了另外事情。
“还多着呢,就惦记着你的烧花生呢。”董桂芳答道,言语里满是爱意。
“那就好,返校的时候我要拿些儿。”明辉高兴地说,忽然,想起一个人——小雪,对小雪肯定没吃过烧花生。但一个问题马上摆着面前,和小雪去哪里烧花生呢?在县城,这还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。
这样琢磨着,马上又一个问题纠结着明辉,我为什么要给小雪烧花生吃呢?难道是她对自己好还是自己喜欢她呢?这真是个让人烦心的事情。回家看到父母操劳的一幕,明辉心里特别不舒服。如果自己不务正业,和小雪整日厮混到一起,能对得起辛苦付出的父母吗?能对得起自己执著追求的文学之梦吗?小雪她有家庭优势,而我呢?难道也像父亲一样,面朝黄土背朝天,在土疙瘩里刨一辈子?看了这个问题自己得好好想一想。
此刻夜色正浓,黑如泼墨。四周不知名的昆虫叫得正欢,灯光晕开的空间又被黑暗随时吞噬的危险,微风习习,凉意从裤腿丝丝升起,如血液在逐渐凝固,直袭心窝。杨明辉和妈妈都不再言语,只有花生沙沙掉落筐子里的声响。